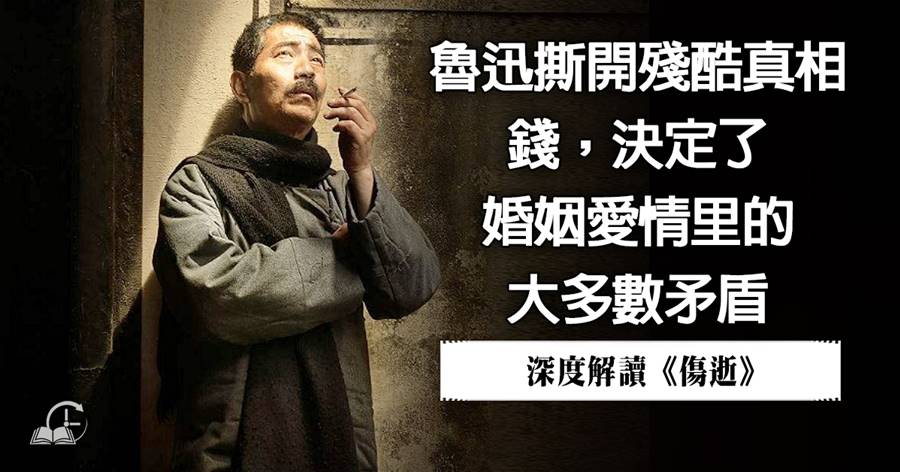
向往中甜蜜的婚姻變得索然無味,不過三個星期,涓生讀遍了子君的身體與靈魂后,便發現以前自認為的「了解」,不過是「隔膜」。不再讀書與思考的子君,并非他理想的靈魂伴侶。精神層面的求而不得令他備感痛苦,子君卻沉浸在她的小幸福里怡然自足。
因與子君不容世俗的愛情,涓生被同事舉報丟了工作。失業帶來的經濟困境,一下子摧毀根基岌岌的感情中勉強維系的平衡。
沉溺在文學創作和求職中的涓生,無以理解子君生活上的捉襟見肘。菜冷,有時竟不夠,他將不滿遷怒于子君的狗兒阿隨,當油雞逐漸變成肴饌,阿隨也被涓生帶去荒野里扔了。冬天愈發冷的難熬,涓生為了逃避冰冷的屋子和沉默的子君,每日躲進圖書館的鐵火爐邊枯坐。

《傷逝》插畫
經濟的匱乏讓養活子君成為涓生最大的「累贅」,想逃避現實,但偽善的良知又使他張不開口。涓生突然想到「她的死」,人性的惡念雖一閃而過,卻如匕首投槍, 精準扎進現實的心臟:愛情在生存面前不堪一擊。涓生潛意識里的黑暗,不過是無能懦弱的私欲,假如子君突然死去,他既逃脫了生活壓力又不必承擔道德的鞭撻。
魯迅洞若觀火的目光,如炬般射進人性最隱秘的陰暗之地。文學自有它偉大的共通之處,陀氏小說《涅朵奇卡》里郁不得志的音樂家,將自己事業的失敗完全歸咎于疲于養家的「世俗」妻子, 最后在理想的圮塌中殺死了她。

不管是以文學為追求的涓生,還是以藝術為信仰的音樂家,都是以完美化的「精神需求」作為逃避的出口,將真實的生活重擔卸給更弱勢的伴侶,試圖以詩意的「痛苦」推諉自身的問題,說到底都是現實的卑怯者。
自由戀愛帶來的進步的激情,在貧窮的催化下余燼將熄。當現實照進理想,曾經從文學小說中形成的狹義的愛情想象,碎成粉齏。 涓生衣衫單薄地偎在破舊火爐邊,清醒地悟出一句:「人必生活著,愛才有所附麗。」
在「生」與「活」之間,人性回歸到原始的最低處,一切內心的不堪都可以自我諒解。

《傷逝》手記體的敘事方式,將涓生完全私我的想法袒露給讀者,內心不堪的隱秘一覽無余,有一點類似「盧梭式」的懺悔。在整篇小說中,子君的形象是很模糊的,子君的情緒回應都是通過涓生的揣測與想象,這使得讀者在理解子君的同時,有一種「不真實」的隔膜感。
在這段愛情的開始與結束的過程中,子君是一個「缺席的敘述者」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