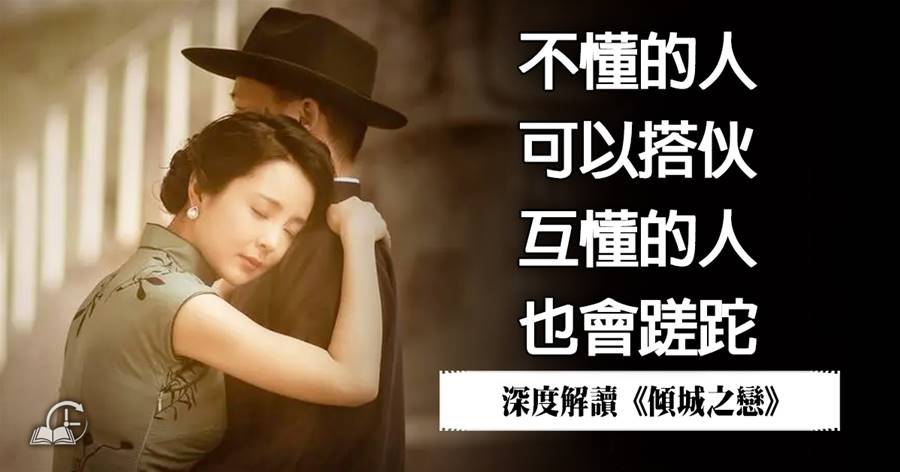
1942年,戰爭已經爆發,23歲的張愛玲被迫終止香港大學的學業,回到上海。
上海已淪為孤島,卻成為張愛玲的福地。
那一年,她文思泉涌,一鼓作氣,為她喜歡的上海人寫出一本本香港傳奇:《沉香屑·第一爐香》《沉香屑·第二爐香》《琉璃瓦》《茉莉香片》《心經》《封鎖》《傾城之戀》。
最具代表性的當屬《傾城之戀》,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:
這是一個動聽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。

沒有愛,原生家庭難以待下去
古人言:窮在鬧市無人問,富在深山有遠親。
故事中的白流蘇,就身處這樣一種人情冷暖、世態炎涼的現實。
出嫁沒多久,因為不堪家暴,離了婚,重回娘家。二位哥哥把她的積蓄搜刮出來做投資。錢用光,開始嫌棄,就差明說讓她卷鋪走人。
沒過幾年,前夫病逝。夫家派人過來,讓白流蘇去奔喪。
一家老小全鼓勵她回去,還「周到地」為她今后生活做出打算,美其名曰,為她考慮。說白了,完全是借此機會將她攆出家門。
她不愿意,嫂嫂們便對她冷嘲熱諷,指桑罵槐,侄子侄女隔岸觀火,白眼相對。
在兄嫂那里受了氣,跑到母親面前尋求安慰。生她養她的母親,說起問題來避重就輕,冷若冰霜,說什麼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,你跟著我,總不是長久之計。」

對白流蘇而言,這樣一個只識金錢不認情感的原生家庭,她實在待不下去了。在金錢面前,哪怕血濃于水的骨肉親情,也會這般不堪一擊。
張愛玲有一篇文章,寫她自己與父親的僵硬關系。記得有這樣一句話,人性的蒼涼與人情的冷暖,都濃縮其中:
血緣只是注定一種關系,如果沒有相互的依偎、溫存和溝通,這種關系也就徒具名分,如塑料鮮花,缺乏光澤。
在此境遇下,白流蘇自然想另嫁他人,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港灣,過一種揚眉吐氣的生活。

一個六親無靠的女人,只有靠她自己
白流蘇與范柳原的結合,是一場陰差陽錯、弄拙成巧的人生戲曲。
原本,范柳原是親戚說給白流蘇七妹的對象。
據介紹人講,范柳原三十出頭,一名產業頗豐的華僑的兒子,事業有成,父母雙亡,思想西化,「年紀輕的時候受了些刺激,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,嫖賭吃喝,樣樣都來,獨獨無意于家庭幸福。」
一頓相親飯吃下來,幾次交際舞跳下來,那個打扮得珠光寶氣花團錦簇的七妹,富二代沒有看中,他暗暗鐘意于親友團里的白流蘇。
全家人勞心費神,興師動眾,本想為七妹釣個金龜婿,結果失敗了。
兄嫂一致認為,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怪白流蘇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