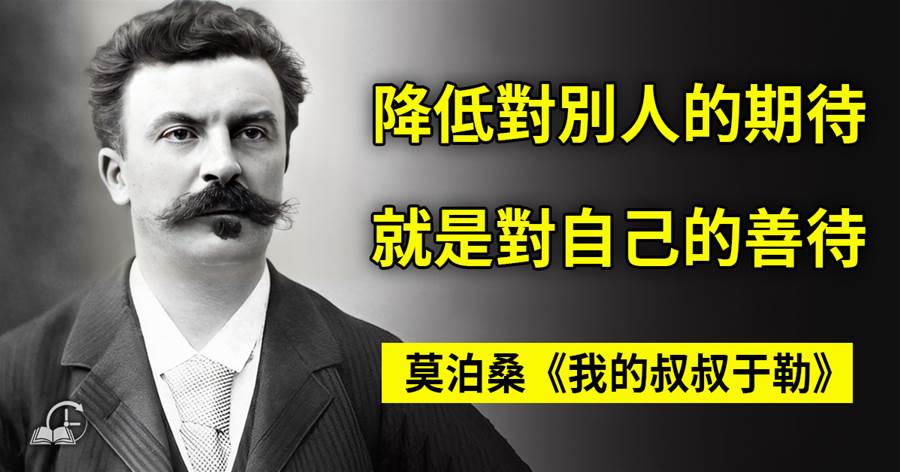
莫泊桑、歐·亨利、契訶夫并稱「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」,其中,莫泊桑被譽為「短篇小說之王」。
張愛玲說:「最好的材料是最深知的材料」,《小團圓》故此成形,因為盛九莉就是張愛玲。
莫泊桑也多從自身見聞中取財,雖沒把自己寫進小說,卻也是因為了解才信手拈來,有以普法戰爭為背景的,有反映小職員苦辣酸甜的,有記錄鄉村趣聞的,有講述愛情故事的,林林總總,莫不有現實生活的痕跡。
而使之與現實拉開距離的,是莫泊桑賦予小說的戲劇效果,就如歐·亨利小說「含淚的笑,結局的出人意料」,莫泊桑的小說也常有悲喜交加的措手不及,如反映小職員生活的《我的叔叔于勒》。作家光怪陸離、精彩紛呈的內心世界由此可見一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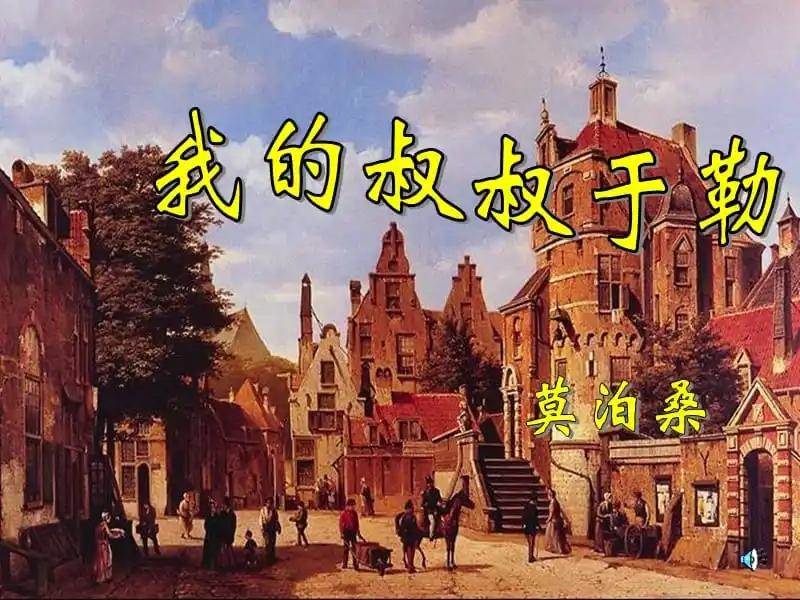
年輕,意味精力充沛,前景遠大;也意味輕浮放浪,行事不加節制,愧悔在早遲之間。
于勒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,揮霍無度,把自己的那份遺產糟蹋得一干二凈以后,又花掉屬于哥哥的部分遺產,絲毫不顧念生在寒門小戶的事實。
在窮人家里,于勒的所作所為無疑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,也就跟壞蛋、無賴、大逆不道沾上了關系。家里人沒奈何,按照當時的規矩,讓他搭乘到美洲去的商船,送他離開出生地。
沒過多久,于勒來信說在美洲發了財,要補償曾因胡作非為給哥哥造成的損失。某位船長也說,于勒盤下了一家大商店,做起了大生意。
自然地,于勒就由家人眼里一錢不值的無賴成了個正直的人,一個有良心的好兄弟,一個無愧家族的好子弟,跟家族所有成員一樣誠實可靠了。
隨著第二封信的到來,家里人更是歡天喜地,把它當作福音書,有空兒就拿出來看看,也拿出來讓別人看看,因為信上說于勒將要去南美作一次長期旅行,發達了就回來和哥哥一起快樂地過活。

約瑟夫小時候,家境并不富裕,只靠父親早出晚歸掙得的微薄的工資勉強度日,少不了處處節省——向來不接受別人吃飯的邀請,以免回請;買日用品,只挑商店里滯銷的打折貨、舊存貨;兩個姐姐自己做裙子穿,購買價格低廉的花邊也要在錢上磨個好半天,雖說大姐快三十的人了,婚事尚無著落,二姐嫁出去了,但也是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勒叔叔的信;家里飲食單一,從不變樣,只在調料上變些花樣,盡管衛生健康,約瑟夫還是寧愿吃點別的,但是吃不到;要是約瑟夫弄壞衣服上的扣子,撕破褲子,準會劈頭蓋臉地挨一頓罵。
約瑟夫的母親因為生活窘迫,經常把丈夫數落一通。每當這時,丈夫囁囁嚅嚅,張開手掌在額頭上搓來搓去,露出無能為力的痛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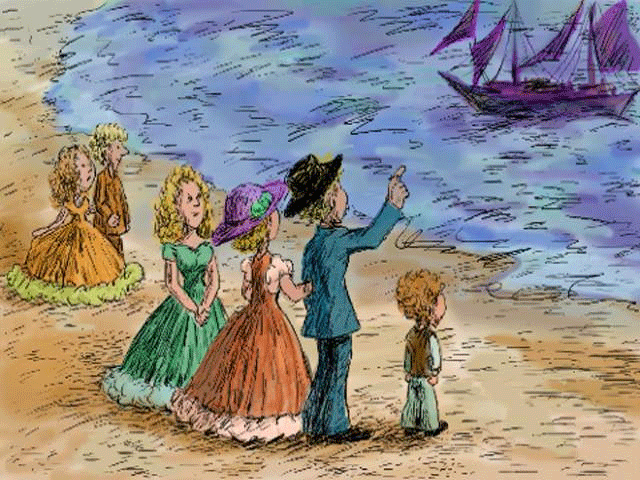
能救達夫朗什家族于水火中的,只有天之涯海之角的于勒了。于勒是那時全家人唯一的希望,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